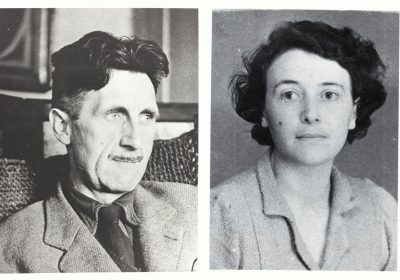寶馬香車,紅粉佳人,滋潤了賽車場上無數觀眾的眼睛。不過,車手時有不文舉動,例如在頒獎台上向賽車女郎射香檳,更有如大會指定動作,多年來受到抨擊,指相關行為冒犯女性。一級方程式(Formula One 或 F1)自從被美國自由集團(Liberty Media)收購後,亦決心洗脫這一陋習。近日 F1 正式宣佈,往後賽事將取消聘用賽車女郎,指這個傳統慣例已不合時宜,有違當下的社會價值觀。贏得衛道人士稱許之際,卻有不少賽車女郎反而表示不滿,認為這除了讓她們丟失工作,同時也根本沒有為她們平反。禁令一下,反而判定了過去的指責言論都屬正確,她們只是被贊助商物化消費,衣著暴露的花瓶角色。

「過去一年,我們在很多方面都作出了檢討,也相信是時候加以改革,令做法更加符合我們對這項運動的期許。」同時,F1 營商總經理 Sean Bratches 於聲明中提到:「聘用賽車女郎是一級方程式格蘭披治大賽在過去多年其中一個最重要的環節,不過,我們開始感到這做法並沒有讓大眾對賽事產生共鳴,而且清楚地偏離了今日的社會氛圍。我們認為這做法對 F1 大賽,以及全世界的新舊支持者來說,已不再合適或如此重要」不過,對於 F1 如此明確否定賽車女郎的價值,將她們與賽事劃清界線,「華盛頓郵報」於消息出公佈後,隨即引述幾位賽車女郎在社交平台的發言,指 F1 的做法並沒有讓她們覺得愉快和受尊重,反而指斥過度的「政治正確」對她們構成了傷害。或者,相對於被選手射香檳,在她們眼中,離地的女權主義才是更大災難。
以賽車女郎為職業的 Rebecca Cooper 在個人 Twitter 上表達了她的反對和憤怒:「慘劇發生了,F1 再不會有賽車女郎。最荒謬的是,最終把我們迫上絕路的,就是這些聲稱『為女性權益而戰』的女人。」「接下來是否要廢除啦啦隊、雜誌女模,然後對女歌手的穿著都有規範?」
另一名賽車女郎 Michelle Westby 同樣質疑,如此「政治正確」地捍衛女性權益,卻讓她們的工作權益和社會地位受到剝削,於經濟和心理上都不好過:「看到那些對賽車女郎的評論,令我非常生氣,我們被嘲笑是無大志、無腦、甚至對跑車和賽事一竅不通。實情是,大部分賽車女郎都對賽車有濃厚興趣,而且很多人都是在日常正職或課餘時間來賺生活費。這些女孩子才不像大家想像中光靠一張臉賺錢。」
「大家都可能忘記了這句話:不要從一本書的封面斷定它的好壞。」Westby 直言,要感謝這群本末倒置的女性主義者,因為不少女性會因此失去基本收入,原因只是男性無法控制自己的言行思想,而她們其實沒做過任何事情,這根本是個笑話。

事實上,自從 2016 年 F1 被自由集團收購後,已為此歷史悠久的賽事作出一連串改革,早前就因為修訂分紅制度,令法拉利車隊強烈不滿,揚言退賽。事關 F1 有意在參賽車隊的商業協議到期後,建立一個新的獎金分配制度,而法拉利車隊將會失去在舊制分紅中所享有的特權。加上 F1 的新東主傾向於往後賽事使用更低價的引擎限制,同樣導致法拉利車隊與主辦單位關係轉差。
一波未平,又起一波,而是次 F1 明確取消聘用賽車女郎,其實是承接了專業飛鏢公司(Professional Darts Corporation,簡稱 PDC)的決定。日前,PDC 就宣佈將不再在賽事舉行期間聘用性感模特兒作宣傳用途,其發言人表示:「在審視了賽事主要播放平台的各種意見之後,我們才作出這個決定。」外界亦相信,兩大知名競賽主辦單位 PDC 和 F1 的決定,或對其他範疇的主辦者產生帶頭作用。
此外,F1 前主席 Bernie Ecclestone 亦不認同新東主的做法。「這個國家,如今變得過分拘謹了。」他質疑為何大眾只針對賽車女郎會敗壞風氣,卻不會批評時裝秀上的模特兒。「不僅車手們喜歡她們,觀眾們也喜歡。F1 就是一場表演,她們也是這場表演的一部分,穿得漂亮的女孩子舉著牌,跟一群車手站在一起,她們並沒有冒犯過任何人吧。」

進一步而言,這不只影響一眾賽車女郎的工作和生計,在社會共識的層面,與賽事無關、不合適、無共鳴的指控,亦反向地賤視了賽車女郎的工作專業,說明過去多年的確一直都在物化女性。不少賽車女郎都不認同這一點,儘管自豪於自己的職業,卻隨著 F1 的禁令而被消去聲音。
F1 事件惹來雙方爭論,或揭示了大眾在衡量性別平等之際,往往忽略了現實狀況。舉例說,前賽車女郎 Charlotte Gash 接受 BBC 訪問時提到:「非常遺憾,對於 F1 屈服於少數人的『政治正確』指責,我很反感。我是比較幸運的,不需要以賽車女郎為主要收入來源,但有很多女孩子需要這一筆薪金。我知道,賽車女郎需要穿得十分養眼,但這是我在賽車場上的崗位,我需要跟人群互動,為贊助商做好宣傳工作。」與做了 8 年賽車女郎的 Lauren-Jade Pope 的憤慨不謀而合,認為批評者只看到她們被物化、消費,或被男性凝視的一面,卻根本未有真正了解賽車女郎的工作以至制服樣式,便以女性權益騎劫了她們的工作權益:「我不曾覺得不舒服。我喜歡我的工作,如果我不喜歡,我才不會做。沒有人強迫我們,這是我們的選擇。」
這無疑是女性主義反被基層女性反噬的一次例證。因為在當下的晚期資本社會,賽車女郎正是一種以情感勞動作為生產力的職業,這本就意味著她們選擇以自身的優勢換取薪酬,並非處於全然被動和受剝削的情況。搬字過紙的物化女性指控,以陳腔進佔道德高地,但對賽車場上的勞動階層來說,未免只是刻板和離地的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