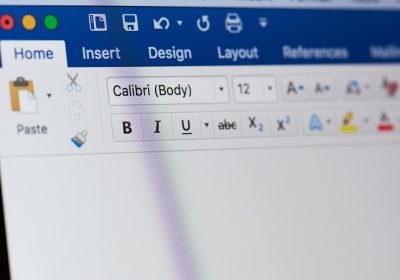在 21 世紀,人類的創意成為了根本的經濟資源,除了傳統的勞動階級(working class)和服務階級(service class),還出現了「創意階級」(creative classes),無論是科學家、工程師、學者、設計師,或者藝術家,只要以創新維生便是「創意階級」一員。倫敦大學皇家哈洛威學院地理學家 Oli Mould 的著作 Against Creativity,引領讀者反思創意如何影響現今社會。
Mould 認為,創作慾望是人類的特質,這種創造力能超越一般的藝術表達,可是「創意」(creativity)的概念,其實是現代資本主義產物,在過去數十年更變成一種空洞而具破壞性的新自由主義價值觀。到現時為止,人們發揮「創意」,彷彿等同要構思新產品和服務,並推出市場。即使做最乏味的工作,也必須具備創造力和企業家精神,為求在一個不穩的經濟環境中生存。即使下班後,創新也成為「類工作」(work-like practice),侵佔休息和社交時間。
這種對私人生活的入侵,很多時是通過智能手機營造的「虛擬出勤主義」(virtual presenteeism)。一方面,矽谷的科技巨頭把創造力吹捧成一種美德,即便喬布斯(Steve Jobs)此類開發人員的發明很多時並非原創,都是在前人基礎上建立新元素,但他們依然受世人景仰,被視為極具創造力、擁有獨創思維的偉人。與此同時,下班後手機程式的演算法,仍會把一種理性的創意生活態度,無意間植入到我們的日常生活中,Mould 稱之為「算法統治」(algocracy)。對於創意階層而言,工作與生活平衡是一個笑話。
在宏觀層面,創意的概念也融入到各國政府的緊縮政策當中,要求社區在更少資源下,付出更多努力。當一些公營機構因為削減資源,而導致服務質素下降,人們就會歸咎於政府缺乏創意。與此同時,創意論述亦應用於推動城市開發和投資。Mould 批評所謂的「創意城市」(creative city)時常淪為「藝術洗白」(art-washing)。一個典型例子是政府找來藝術家,做一些「無害的街頭藝術」,來營造「一個前衛創意城區」的假象,但同時迫使小租戶遷出,讓富人搬進新建住宅。
不過,Mould 並非完全要摒棄創意論述,而是希望從根本反思創意的定義。他鼓勵人們不應盲目將創意和生產力相提並論,而是要運用一己智慧,思考如何組織各方,以及如何建構新的生活模式。相對於帶新自由主義色彩的創意,Mould 更主張培養一種激進的創造力,以打破我們既有的組織模式和消費習慣。
書中提出幾個符合 Mould 所定義的「創造性」社會項目,例如阿根廷的復興工廠(Recuperadas) 運動,工人們接管工廠,實行自治生產模式。2008 年英國陷入金融海嘯,倫敦布里克斯頓區的居民就推出區域貨幣 Brixton Pound 支持小店經濟。另外,民間組織 UK Uncut 就曾把巴克萊銀行分行變成圖書館,以對抗大企業的逃稅行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