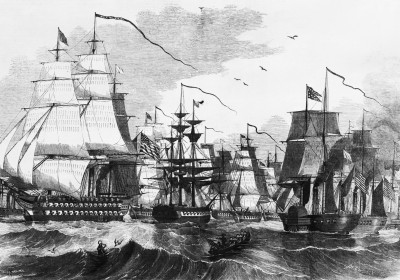亂流之下,反烏托邦經典如「一九八四」和「美麗新世界」再度暢銷,讀者總著眼其社會批判能力,卻沒多少人欣賞烏托邦小說,斥之為過於天真。美國文化周刊「國家」(The Nation)就為此平反,文章認為兩者是一體兩面,烏托邦小說同樣是建基對現實的批判,往往誕生於山雨欲來的時刻,可激發人民變革的想像力。

1516 年英國作家摩爾(Thomas More)創作的「烏托邦」(Utopia),被奉為近代烏托邦小說的濫觴,但很多人忽略故事開場,其實描繪了一個反烏托邦場景 —— 歐洲在戰爭和赤貧下四分五裂,圈地運動持續,甚至有「羊吃人」的恐怖下場。人類必須在滅頂前尋找替代的社會方案,摩爾從而提倡一個社會平等、財富共享的「烏托邦」。
由此可見摩爾對烏托邦的想望,其實源自對反烏托邦的恐懼,渴望人類開創充滿可能的嶄新未來。此後數百年間,無數個人間天堂與人間地獄在人類筆下誕生,部分人更把烏托邦理想付諸實踐,結果卻往往換來反烏托邦的現實,以致很多人如今都對烏托邦喪失信心。
在政治光譜上,無論左右翼都有人反對烏托邦幻想。鐵娘子戴卓爾夫人就以著名口號「別無選擇」(There is no alternative),揚言一切烏托邦計劃注定要失敗。即使是馬克思本人,在世時亦多番用「烏托邦社會主義」的稱呼,批評法國哲學家傅立葉(Charles Fourier)和聖西門(Henri de Saint-Simon)的理想社會藍圖,只憑空構想而不切實際,馬克思以此標榜自己提出的社會主義建基於科學,符合人類歷史發展邏輯。
「進步就是邁向烏托邦的過程」
事實上,過去數十年間,反烏托邦想像確實主導了我們的文化,無論是虛構的小說還是紀實的新聞,同樣充斥著氣候災難、核災難、病毒大流行、極權統治崛起等訊息,現實荒誕得有如反烏托邦的小說情節,我們都缺少走出困局、建設另類制度的想像力。
文章提醒,雖然現實中的烏托邦期許,確曾帶來過災難後果,但徹底摒棄烏托邦願景的世界,終究也使人類跌入絕望的泥沼。政治學家 Lyman Tower Sargent 便對烏托邦抱持較正面的看法,認為它可磨練我們擺脫現實的想像力、學習為自己爭取更多權益、質疑不公義世界的合理性。愛爾蘭作家王爾德(Oscar Wilde)更如此說道:
一幅不存在烏托邦的世界地圖,根本不值得一瞧,因為它遺漏了可供人類登陸的國度。一旦登陸以後,人類便會四出張望,在找到另一個更好的國度後再次啟航。所謂進步,就是邁向烏托邦的過程。
回顧歷史,烏托邦創作也通常源於對現實的批判,歷史學家 Perry Anderson 便梳理出烏托邦與現實的微妙關係 —— 摩爾創作「烏托邦」同時,撼動歐洲的宗教改革已蓄勢待發,摩爾將因此犧牲;被指顛覆西班牙統治的意大利修士 Tommaso Campanella,1623 年撰寫「太陽城」(City of the Sun)描畫理想社會圖景,時值拿坡里起義前夕;法國大革命爆發前的 1772 年,啟蒙思想家狄德羅(Diderot)把性解放主張寫在「布甘維勒之旅補遺」(Supplément au Voyage de Bougainville)之中。
在思潮澎湃又社會動盪的 19 世紀,烏托邦創作亦如雨後春筍,如英國小說家 William Morris 的「烏有鄉消息」(News from Nowhere)和美國小說家 Edward Bellamy 的「百年回首」(Looking Backward)。遠在亞洲的康有為,也在清朝維新失敗後、皇朝覆亡之前,寫出驚世駭俗的「大同書」,提倡摒棄家庭制度以消弭貧富等大膽主張。
正如摩爾筆下的「烏托邦」以反烏托邦惡夢開首,反烏托邦小說也有暗示反抗的可能、邁向烏托邦的出路,兩者存在一體兩面的辯證關係。無論烏托邦還是反烏托邦小說,其實同樣帶有現實批判意識,有著互通的終極人文關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