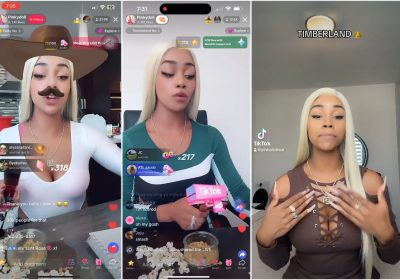普林斯頓大學前教授余英時出版回憶錄,講述他年輕時進入燕京大學,一度受左傾思想短暫洗腦影響。
時代的瘟疫席捲全球,由 19 世紀末的無政府主義開始,一直到 20 世紀初的共產主義。巴金的「家春秋」小說三部曲,反抗封建禮教,加上魯迅的「狂人日記」,將中國傳統倫理文化一概定性為吃人的惡魔,有足夠的空間,輸入那時歐洲興起的政治虛無極端思想。
在那個時候,北京上海的青年學生如果不趕上這班時代的列車,就被視為落後、守舊、老餅。
如何叫做洗腦?好像小孩出麻疹,或一陣流行性感冒,導致類似邪靈附身的狀態。即使有天主教神父趕到驅邪,「受害人」也像變成了另一個人,用粗言穢語,向神父發出詛咒。
余英時憶述,在北京的時候,一個牧師剛由安徽回來,探訪他堂兄。牧師在講述目睹鄉間的教堂和信徒被共產黨幹部迫害之種種,年輕的余英時突然大為憤慨,覺得這是國民黨造謠,以嚴厲的語調,直斥這位長輩。但長大後想當年,他為當時的失態感到內疚。
幸好此一狀態為時甚短,余英時一度北上迎接新中國,火車到石龍,故障停車。就在那一刻,余英時反覆思考,及時回頭,回來香港,進入新亞書院跟隨錢穆之後,很快就回復正常。
到底這種激進左傾意識形態,為何能在短時期席捲民國時代知識分子的大腦?
余英時認為:因為孫中山的三民主義思想,早有「天下為公」的訴求。而「天下為公」也是禮記的第一句理想:「夫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然後中國早年的知識分子就以為共產主義等同中國遙遠的儒家理想:人人有飯吃、財富分配平均、公平公義,萬事大吉。
但中文的缺陷,就在這裡:你可以說老子的一句「上善若水」,用字比英文精煉,包含了非常豐富的哲理,但也可以說太簡單的四個字,還有大量空間,缺乏細節,須要進一步的詮釋。
中國文化由中醫到烹飪,都只講「意會」。「意」,是一種主觀的臆想和感受,不可以定義言傳。廚師炒菜油鹽糖放多少,有如莊子裡的庖丁解牛,用刀講心法,憑感覺就知道牛的筋骨在何處。中醫把脈,片刻就認為病人有了「虛寒」,並無體溫數字,也沒有 MRI 之類的掃描報告佐證。
西醫認為:量體溫知寒熱,寒就是寒,無所謂虛寒。熱就是熱,無法定義何謂「虛火」。中國語文決定了中國人的思維模式(mindset)。
中國許多工藝,都講意會。酒家從前招聘大廚,只讓廚師考一道揚州炒飯,另加豉椒牛肉,除了看刀剁砧板工夫,還看菜式「鑊氣」,以判斷技術高下。
「天下為公」是一個粗淺的大概念,實在缺乏內容。在西方學術角度,這四個字不足以成一部理論,需要不斷的論證和詮釋。
但 20 年代,中國的知識分子憑這句古訓的感覺,就認為馬克思列寧那套可以解決中國社會千百年貧富不均的問題,實在幼稚。
這一切,又以中國語文的象形結構決定。中國文字長於感性,理性的詞彙不足。感性先行,對於理想和理念,即容易被一人掌控了話語權,成為教主,知識分子率先,即走入魔道。
甚麼叫「天下為公」?北歐的瑞典芬蘭挪威,用養老金、免費醫療、免費教育等,加以重稅,早已實踐了此一理想。其中不必流血的探索,也不必內戰和暴亂。
這一切,當年的知識分子如果去一次北歐,去一次英國和美國考察,包括余英時,回來中國,或可以想通很多,就能避免一段血腥的彎路和歪路。
余英時是今日華人世界,僅存對中國傳統文化了解最透徹之人。唯智者如此,年輕時也難免中招,何況庸人滿街的今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