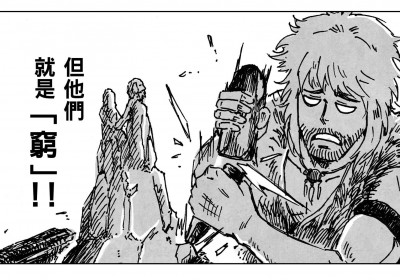最近讀錢鍾書《宋詩選注》。第一個感覺是,竟然有那麼多農事詩。題材之所以勞歌憫農村居田家為主,春思秋聲野望郊遊為輔,選目被批「迎合風氣」,當然與出版年份 1958 年「學術界的大氣壓力」有關。「由於種種緣因,我以為可選的詩往往不能選進去,而我以為不必選的詩倒選進去了。」88 年港版序錢鍾書歎詩集過時,不免淪為當時學術風氣「半間不架」的文獻。
三十年為一世。如果說 1958 年政治主宰文學,前後一世則見證了泛政治化的興起與衰落。
1928 年,創造社等左翼文人從日本引入「普羅列塔利亞文學(Proletarian literature)」,提倡以階級觀點書寫「與無產階級解放有關的一切」,掀起一場文學革命,而文學革命即革命文學。一連串論爭席捲中國文壇,參與者眾,右翼作家如梁實秋少不免挨批,左翼如魯迅亦難逃革命派非議:「思想停滯」、「阿 Q 時代是早已死去了」(錢杏邨)、「二重的反革命的人物」(郭沫若)。有說 1928 年為普羅文學興起之始,若說當時文壇還算眾聲喧嘩,時至下世,革命派已告全面勝利。
按文學史脈絡而言,中國傳統詩論到清末民初經已式微,同光體詩人陳衍就被王德威視為「傳統詩話的最後總結者」。陳衍以「三元說」(開元、元和、元祐)解讀唐宋以來文學流變,認為宋代「學人之詩」接續於唐朝「詩人之詩」乃歷史必然發展,主張兩者合一,既「吟詠情性」亦「明志見道」,背後本於一種「『求真』的本體論式的憧憬」。照錢鍾書所述,歷代文人對宋詩毀譽不一,南宋金國鄙其「衰於前古…… 遂鄙薄而不道」,明人李攀龍所編歷朝詩集甚至直接跳過宋詩;及至晚清,同光體推崇之下,「宋代詩人身價十倍」,江西派黃庭堅詩集一本就賣過十両。而無論褒貶何如,各家始終注重文學精神,並不脫「傳統文論的寄託」。
到錢鍾書,《談藝錄》承襲傳統詩話形式,內裡卻已「奪胎換骨」,挪用現代西方文學定義,以形式主義評估中國詩論,唐宋之爭由文學精神之爭一變為文學形式之爭,「真實懷抱、真實道理、真實本領」(陳衍語)不再重要,無病仍能呻吟才是好詩人。由三元說到《談藝錄》,「真實寄托已經產生了位移」。然而革命大纛底下,形式主義要讓路,同一個錢鍾書縱「忍不住自作聰明,稍微別出心裁」,不免也要引用延安文藝座談會語錄,點評一下文學如何回應階級矛盾。當過去成為舊世界,傳統文學觀不改頭換面就隨之入土。
1988 年 6 月起,陳思和、王曉明於《上海文論》發表近 40 篇專論,探討「文學的形式、主題、大師、經典,乃至於迂迴於文學背後、支撐文學發展的種種歷史因素」。王曉明所言「文學不是『遵命文學』」,「要否定政治決定論,書寫不應該受制於意識形態,同時要拒絕『起承轉合』的機械進化論」等一系列「石破天驚」的倡議,呼應了 80 年代政治自由化的風氣,爾後至今,「重寫文學史」的計劃不絕於途。據張泉統計,自 1951 年至 2007 年間,中國大陸出版的文學斷代史論最少有 119 本。
又過一世,文學傳統/傳統文學的面貌重估得如何?我不知道,文學世界之大千駁雜,或者亦無人可以斷言。單憑近年出版刊物而言,傳統文學評論似乎泛起一陣復古風。僅舉兩例,一是方法論的返祖,二是舊學人的招魂。
「知人論世,以意逆志」
李劼新作《心聲與情物》專論唐宋詩詞,顧名思義,詩乃心聲,與個人生平遭遇密不可分;詞乃情物,與政治無涉。按其分析,政治詩不值一顧,抒情詩才是精華:杜甫的「賢臣夢」「幾近瘋癲」,只落得茅屋為秋風所破之狼狽失態,「煌煌言志之詩」如〈麗人行〉、〈兵車行〉,不過是傻儒生的「光榮傳統」,「可敬而不可愛」,李劼最欣賞的是即景詩〈春夜喜雨〉、〈春望〉、〈登高〉,喜其字斟句酌;李白則是一心發俠客夢,寫詩僅是愛好,「好看好玩」處不在述志詩如〈俠客行〉、〈行路難〉,而在「任性」、「擺脫俠客與詩人糾葛」之作,尤以吟詠大自然與抒情為上乘(〈望天門山〉、〈月下獨酌〉)。
「杜甫與李白…… 一個要成為驚世駭俗的俠客,一個要成為萬古流芳的賢臣;而寫詩,其實只是他們的業餘愛好而已,假如連這都弄不明白,那麼他們兩個的詩真是白讀了。」李劼詩話襲用詩言志的傳統,卻不按成見發論,甚至反其道而批評之。從杜甫樂府讀出「孟軻式民本立場」、「女禍的傳統之見」,由李白述志詩看出「一廂情願式的無厘頭」,以詩證史,以史論詩,做法可上溯於孟子的「知人論世,以意逆志」。然則方法論復古,結論可以很聳人。當讀到杜甫絕聯乃是「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無法想像還有更為出色的詩句能出其右」),不禁令人佇立茫然。
「唐人重感,宋人重觀」
近年不少民初文論重刊,顧隨《蘇辛詞說》是其一。身為 20 世紀前半葉的國學大師,顧隨自然秉承傳統詩話體系,然而發論毫不一般,亦遠非保守:辛棄疾「鋒芒四射」,蘇東坡「圭角盡去」;「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而辛詞「只作到個當行即得,不自在也罷」;辛渾融圓潤,偶有拙筆但無俗筆,蘇縱有豪氣雅量,然浮淺俗筆繁多,〈定風波〉、〈念奴嬌.大江東去〉更是大俗,詞才遠不及辛棄疾。顧隨不似李劼語出驚人,對今日主流文學觀仍然衝擊有餘。
顧隨於宋詩亦有著述。顧隨反對「宋詩說理,唐詩不說理,故宋不及唐」的說法,認為知(理智)、覺(感覺)、情(情感)「相濟而不相害」,詩情與哲理通。兩代分別在於「唐人重感,宋人重觀」,前者屬情,後者屬理:「蛛絲閃夕霽,隨處有詩情」(陳與義)是觀察,屬理智,「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飛」(杜甫)則「似觀而真是感」;「宋人詩有輪廓…… 唐人詩則繫變化於鬼神」;宋詩理智發達,獨擅修辭,工於詩學,結果是多偽詩而少真詩。陳衍以為詩史向前,唐代詩人之詩將情與景寫絕了,後人自然發展出「長於意理、講求詩法」的學人之詩;錢鍾書則認為既有唐詩榜樣,宋人「就學了乖,會在技巧和語言方面精益求精」,同時「也偷起懶來,放縱了摹仿和依賴的惰性」;顧隨則說「宋人對詩用功最深,而詩之衰亦自宋始…… 凡一種學問成為一種學問時,已即其衰落時。」三人之中,然而一位以歷史進步論合理化變革,一位看出其時代創造性,不過成就僅在「小結裹」而非「大判斷」,另一位則以共時美學體系觀照詩論,相信唐宋之迭變實為不幸。
以上無法囊括近年詩詞研究的眾多有趣論述 —— 例如饒宗頤的文學觀、徐瑋追述晚清詞如何因時局變革而突破「文小質輕徑狹意隱」格局的《世變、抒情與晚清詞之書寫》—— 僅舉李劼顧隨為例,純為指出傳統詩話或許並未隨陳衍而總結,新人獻猷舊人還陽,究竟是斷代失憶還是隔世招魂,似乎尚有重新闡發的餘地或回應的必要,現代文論對舊學的影響尚有待釐清的空間。譬如若說顧隨重「當行」多於「自在」可以是個人取向,亦可以是進步思想的體現——畢竟顧隨會援引列寧論文學——「蘇之自在,辛之當行」一語引自嘉慶文人周濟,則見傳統詩話可以從來「進步」,不待西學東漸。復古風起,從傳統詩話汲取活水以重寫文學史,可能就是今世的文學面貌。
參考書目
- 錢鍾書 《宋詩集注》 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1990
- 李劼 《心聲與情物 —— 唐詩大觀、宋詞縱覽》 香港: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
- 顧隨 《蘇辛詞說》 香港:香港中和出版,2018
- 顧隨 《顧隨:詩文叢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7
- 謝泳、蔡登山編 《最近二十年中國文學史綱》 台灣:秀威資訊,2012
- 王德威 《現當代文學新論:義理、倫理、地理》 北京:三聯書店,20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