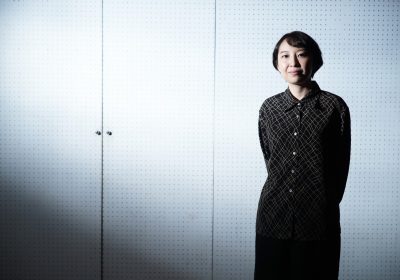「安樂死」,似乎是因重病、老邁、死別而生無可戀者「好死」的代名詞。在最理想情況中,安樂死合法化讓我們掌握死亡自決權。然而當法律賦予我們安樂死的權利,又如何不讓它成為一種對社會和家庭的義務?多年悉心照料重度智障女兒的兒玉真美,作為病人母親與照顧者,將對世界各地有關安樂死議題的所見所聞所想寫成書作「死亡自決權:除了放棄活下去之外,沒有別的選項了嗎?」,說出「安樂死」二元論之不必然。其實,好死與賴活兩個看似非黑即白的選項之間,還隱藏了很多問題。
關於是否為「安樂死」立法的爭論在全球已非常普遍,少數國家如荷蘭、比利時行之經年。然而我們不知道的是,被我們統稱「安樂死」的善終方式實際在全球各地可以有不同定義。根據兒玉真美書作的定義,南韓早前通過讓患者自行選擇放棄治療的「延命治療決定法」,是為「消極安樂死」;「積極安樂死」指為患者注射藥物造成其死亡,是荷蘭現行做法,也是一般人所指的「安樂死」;在美國華盛頓和瑞士被稱為「尊嚴死」的「醫師協助自殺」,是患者透過服食醫生開出致死藥物自殺。至於在討論「安樂死」議題時常被提起的「安寧和緩醫療」,則是以降低痛苦、提高病人生活品質為前題,讓病人自然步入死亡,並不屬「安樂死」。目前香港法律並不容許安樂死,現行只有「安寧和緩醫療」,同時根據普通法,在特定情況下允許「終止無效治療」及「病人拒絕治療」。
「安樂死」與「安樂死立法」的分別
在這個世代,8 成人在醫院,苦於「多餘治療」,直到臨終前仍全身插滿維生喉管,苟延殘喘至生命最後一秒。因此不少人視「安樂死」為擺脫病苦、有尊嚴地死去的一途。不過,也不乏贊成安樂死的人反對為之立法 —— 因為他們預視到立法後,安樂死將由重視個人意志,演變成逼傷病者「不獻世」的義務。安樂死選項的出現,「活不好可以乾脆死掉」的心態便會在社會潛移默化,重病藥石無靈、年老致身心不自由、天生殘障等等受家庭經濟、情感負擔及輿論重壓的病人,即使仍有求生意志,最終還是為了照顧其他人的感受而不得不安樂死,最終還是無法真正自決死亡。
成本論與功利主義
從病人眼中看,安樂死是個人選擇;從部分推動立法的人群來看,卻是減省資源「浪費」的手段。2008 年 9 月英國知名哲學家 Mary Warnock 就說:「為了避免造成國家與家人的負擔,失智症患者應該負起選擇死亡的義務。」2013 年日本時任副總理兼財務大臣的說法更露骨:「想到高額醫療都是靠政府的錢在活,我就睡不好,得早早讓他們死掉。」更有甚者,將安樂死連結至器官捐贈,例如比利時的安樂死申請表,就附帶器官捐贈同意書,叫人不得不聯想到其利益最大化的經濟考量,既可節省醫療開支又能增加器官供應,堪稱一石二鳥。但話說回來,安樂死的人究竟是死得安樂,還是死得便宜?
社會討論、醫護心態與病人的心靈滑坡
以「更好地分配社會資源」為理據來支持安樂死,不單將民眾分等分級,更會在不自覺間,將愈來愈多人主觀納入需要放棄「分薄公共醫療資源」的低級人群中。部分容許安樂死的國家,將「末期重症」定為批准安樂死的主要準則。然而即使爭論至今,何謂「末期」仍然眾說紛紜,而且對象範圍正不斷擴大。最初是末期重症,然後漸漸地,類植物人、失智症、長期卧病在床者也成為對象,標準不停退守,滑坡不斷。根據 2012 年比利時發表的安樂死法十年報告,比利時「安樂死法」通過後,安樂死的執行對象,就慢慢從既定的患「威脅生命的不治之症」、需承受「難以忍受、無法消除與減輕的痛苦」,自行擴大至複數的疾病,和未來可能陷入意識不清、需要照護、失智症惡化的病人,甚至出現未經當事人同意執行安樂死的情況。
比利時的情況,應驗了美國生物倫理學家 Ezekiel Emanuel 1997 年於雜誌「大西洋」針對安樂死立法撰文時的預言:
一旦合法,醫師協助自殺與安樂死就會成為慣例。久了之後,醫生不會再抗拒注射藥物結束病人生命,美國國民也不再抗拒安樂死這個選項。等到大家都習慣了,我們就會把這個選項擴大到從社會的角度看來正在受苦、人生沒有目標的人身上吧!
作為前線工作觀察者,美國華盛頓一家老人院的老闆 Juan Carlos Benedetto 見證當地「尊嚴死」立法後醫護人員工作態度的滑坡,促使他在 2012 年蒙大拿州公投「允許協助自殺」之際,投稿當地「波士頓環球報」:
自從「尊嚴死法」通過之後,我發現一些醫護人員早早開始準備嗎啡與安寧和緩醫療,放棄積極治療。有些醫護人員甚至不向住戶與代理的家屬說明,就擅自開始安寧和緩醫療。我還看到一些醫護人員認為高齡患者的生活品質過低,所以完全放棄治療患者……我們總有一天會老去,我希望到時候能接受治療與照護,也希望自己的選擇得到尊重。這些改變令我心痛,也希望貴州的居民能阻止協助自殺。
真實的本願:求死之人所求為何
兒玉真美翻閱眾多討論安樂死的書籍,認為病人之所以求死,歸根究底都是醫院醫療方式出了問題。維生至上,視病人死亡為醫療失敗,讓醫生只求為病人續命,忽略了每一位病人真正的需求,容易過度醫療。例如明明還可以進食,卻為了方便醫院營運而做胃造廔(不經鼻及食道進食)手術、「不考慮後果便安裝人工呼吸器」,造成不必要的痛楚。如果希望患者從無謂的苦楚中解脫,在討論安樂死前,真正該談的是如何改變目前的醫療方式。香港至今仍未承認安樂死,便是認為病人之所以求死乃過於痛苦之故,該做的是想方法減低病人痛楚,而不是安樂死。
她出書之際也問出關於安樂死最根本的問題:「除了放棄活下去之外,沒有別的選項了嗎?」二選一之外,必定還存有其他選項。兒玉真美此作,雖然充其量也是從一人(或一群人)觀點出發詮釋安樂死,不一定能代表所有病患與家屬的心願,但不也印證了人類對「死得有尊嚴」追求的多面性?這也解釋了為何追求安樂死的人也不一定樂見安樂死立法。正如同時是罕見疾病病友的病人自主研究中心執行長楊玉欣,在推薦序所寫:
疾病對於每一個病人有著獨特的詮釋與影響,如何尊重每一個病人在疾病歷程中所淬煉出的意願、感受、價值觀,而非草率地批判病人的感受與決定,或者權威式地提供不足或過度的醫療,這是每一個他者都應該試著設身處地同理與了解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