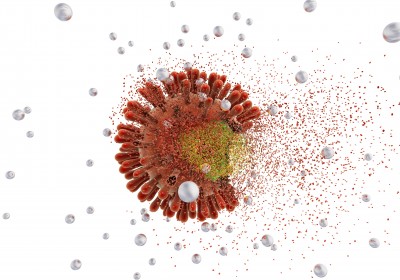我們活著,感受不到腳下的國家/
十步之外就聽不到我們的話語/
而只要哪裡有壓低嗓音的談話,就讓人聯想到克里姆林宮的山民/
他肥大的手指像黏糊糊的蚯蚓/
他的言辭如砝碼般堅實/
在他的蟑螂觸鬚的鬍鬚裡有著一絲/
笑意,他的馬靴發出微光/
一群細脖的跟隨者圍著他/
他奴役著這群半人的僕人/
有人啼囀,有人啜泣⋯⋯
這是一首致命的詩。當時奧西普.曼德爾施塔姆(Osip Mandelstam)寫這首「史太林諷刺詩」,無異於窮盡力氣狠敲史太林,但手中木棍終為燒死自己的火助燃。曼德爾施塔姆因褻瀆史太林被捕,並被監禁至死。其妻子和支持者將詩縫進鞋子,藏進床褥、平底鍋,還有連世上最機警的密探也無法查到的地方 ── 將詩銘刻於讀者的腦中。他們冒險偷運這種無形的貨物,讓詩句得以流傳至今。當時將被禁文學複製並散播的,便是蘇聯的地下出版「薩密茲達」(Samizdat)。
無數「自行出版」串聯而成的抗爭
「薩密茲達」在俄語中指「自行出版」,與意指「國家出版」的 gosizdat 相對。其涵蓋的出版物很多,包括宣揚政治主張的短文、小說、詩歌、演講辭、音樂等。雖然其多指蘇聯時期的出版行徑,但俄羅斯地下出版(或秘密出版)的歷史其實源遠流長。在 19 世紀末,學生廣傳譴責沙皇的自製小冊子。1905 年革命失敗後,言論自由重新受到打壓,但含顛覆性言論的刊物仍廣泛流傳。布科夫斯基(Vladimir Bukovsky)簡單地形容「薩密茲達」:「我自己寫,自己編輯,自己審查,自己出版,自己派發,自己付出因它而被監禁的時間」。話雖如此,每個複印這類刊物的人都有機會身陷囹圄。因為大部分的打字機皆需要向國家註冊,所以若作品在流傳中途被截取,則可被用以追溯至原作者或複印者。複印者亦會將後備的複製品印在縮影膠片上,然後偷運出國付梓,再偷運回國傳播。
地下出版的刊物是甚麼樣子的?
當時以「薩密茲達」形式出版的書和小冊子都以碳紙印製,最多只能印十頁。為了盡用空間,印刷者會將字拉至頁面最邊緣,不留白邊。因為經常有紙張短缺的情況,所以如果印刷者購買數量超過一定數額,被揭發的風險便會攀升。「薩密茲達」生產鏈中每個「接收者」各印製最少四本,亦在事前被警告不要嘗試追溯作者。整個地下出版的手法缺乏組織而且倉猝,因此產物通常有字體模糊、紙張起皺、封面不倫不類的特點,久而久之成為了一種文化標記。

複製的過程中,因原作者無法監察,複製者有機會自行對文本作出刪減或修改。很多作家為了自身安全著想,都會使用筆名,或是拒絕被引用,才導致「作者權限」(authorship)這樣麤疏。共產黨也曾指在剝削知識產權(intellectual copyright)下傳播刊物不公平,使作者沒得到應有的酬勞,意圖藉機打擊地下出版的發展。
愈撲熄愈猛烈的「薩密茲達」
赫魯曉夫上台後,在 1955 年終止了古拉格系統(gulag system),停止對異見人士勞改營形式的政治迫害,出產與官方路線迴異的作品不再是死罪,「薩密茲達」一度興盛。但赫魯曉夫的開放態度惹來不少強硬派人士的不滿,1964 年他終被布里茲尼夫(Leonid Brezhnev)取而代之。在後者管治下,審查制度重新升級,諸多異見人士遭監禁或流放。1965 年,兩個作家因以筆名在海外發表小說被捕,詩人 Alexander Ginzburg 和 Yuri Galanskov 取得閉門審訊的抄本後,將該場審訊編錄成書。這次打壓行動引爆俄羅斯 30 年來第一場自發的政治抗議,隨之而來的是兩封以「薩密茲達」形式流傳的公開信,其中一封懇求布里茲尼夫不要重回史太林主義(Stalinism),由知名文化界人士聯署,其中一位為著名作曲家蕭士達高維契(Dmitri Shostakovich)。
更嚴厲的審查制度適得其反,刺激了「薩密茲達」的滋長。1968 年,莫斯科一群知識份子發起名為「Chronicle of Current Events」的期刊,持續發行 15 年,出版了 65 期書刊,記錄涉及 753 位被告的 424 場審訊。期刊編輯從未提倡顛覆政權,理應符合 1936 年的蘇維埃憲法;但最終期刊編輯及投稿者都被政府送進勞改營、精神病院,或遭流放。截至 1985 年,蘇聯國立列寧圖書館藏有超過 100 萬份被禁文件,被放置於限制存取的館藏區域。
戈爾巴喬夫上任後,推行有名的「經濟改革」(perestroika)和「開放政策」(glasnost),「薩密茲達」才得以發展蓬勃。
地下出版是蘇聯解體的致命因素嗎?
雖然不少人認為「薩密茲達」在削弱蘇聯政體中發揮了關鍵作用,事實上其影響力難以評估。烏克蘭記者 Vitaly Korotich 這樣形容:「蘇聯是被資訊摧毀的 ── 而整個浪潮由索贊尼辛(Solzhenitsyn)所著的『伊凡·傑尼索維奇的一天』開始。」雖然「薩密茲達」出版物只接觸到很小的群眾,但當中許多都是具影響力的文化人士,甚至連某些政府官員都是讀者。
出版令思想的傳播變得可能,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說法是,更能為生活在同一個空間的人創建「想像的共同體」。無論在任何時代,出版都是一項偉大的產業。在局勢嚴峻的時代,出版更是最大的掙扎與反抗之一。